石楠花开的季节,空气中渗透着侵略性;烈日高照的日子,热浪也充满侵略性;止不住的回头看,却不停地被摆正脑袋,时间也具有侵略性。
片段
周末回出租屋拿东西的时候,在路上看到这么一番景象,不知道为什么总觉得很难忘。
我坐在我的龟上,刚刚从小区的大门拐进来。
左手边车站似的,立着的公告牌边上坐了一排排退休的老人——仿佛我每次来到这个车路口,看到的都是这么一番景象。大概在结束了大半辈子的劳作以后,回望走过的路,ta 们发现一切的一切都是公告牌下这张椅子的前奏。椅子背靠公告牌的塑料窗板,公告牌背靠树枝;人坐在椅子上,好像把树的根长在脚底下;隆起的脊背的弧面,与椅背上的栅栏相切;双臂像是液压杆一样撑在双膝上,只不过润滑油已经流尽了,支着身体的已经不再是足劲的气力,而是锈蚀的粗糙。装满了生活路径的脑袋再也抬不起来——并非是失去了生气和活力,我听得到 ta 们仍然健谈——只是那是个直角的角落,再怎么后仰,椅背也会早早拦住 ta 们,不许 ta 们倒向过去,况且就算椅背没了,那些软韧的塑料窗板也会将 ta 们兜住。倘若一定想抬头看到枝叶,以想起自己为何要生脚底的根,那就必须将身子往外挪,好给上身留出倾斜的空间。
但并没有必要,因为只看投下的影子,不仰头,ta 们也知道,老枝上的叶子,是绿色的。
右手边,我已经忘记那些店铺是仍然开着的,还是已经挂上了锁头,反正钥匙并没有插在锁眼里——说来钥匙只有在关键的时候才会被想起。
过去的几个月数次从这个路口拐进来,两侧的景象已经在脑海里受曝了一次又一次,然而总是左侧的致密,右侧的疏松。像是受之吸引,重心歪斜,我的上身连同车身,总是向左侧倾斜,拐入下一个路弯。
倘若不是急着送外卖,在老旧小区狭窄的路上最好还是不要做些艺高人胆大的事情。本该奔驰在更广阔路面上的人造野兽,如今像是聚在荒原细流边上饮水的兽群一样,把笔直的道路啃地宛如肠胃或是迷宫,它们会阻止你看到你应该看到的一切。我正在拐过垃圾站时,一只三花猫从前面不紧不慢地路过,它大概是知道我也急着赶路,不愿在短期规划中插入一场悲剧,不然绝不会如此有底气地横穿马路。朝它走向的地方看去,一位满头花白的老妇——先前被高顶的黑色轿车挡住——像是柱子一样直直地立在路边。她戴着也许是红色、也许是橙色的橡胶手套,粗圆的手臂——又或许是裹着厚厚的衣服——也直直地垂在身体两侧。天地的压力将她的神情压成一种浑厚的严肃,皱脸被端端正正地镶在半空中。只有她的眼睛,斜斜地看着那只猫从“细流”的对面,慢慢踱步到她的身侧,再走到我无法目击的地方去。
此时,我已经拐到了下一个弯。我总觉得自己被拴在了那个拐角,拴在了那老妇人身上。抵住车把的右手抽搐似的涌上阵阵脱力,然而料想的失速却迟迟没有到来,只有我的脑子在不停地告诉自己,一定要马上将这一幕记下来。
距离写下这件事,已经过去了四天。我仍然不明白为什么这一幕让我印象深刻,而在我不争气的记忆世界里,那位老妇人的塑像的细节几乎散尽,只留下一尊规则的几何体,和斜斜的目光。
由片段展开
上面这几段大概并没有非常明确的意图,纯粹是任由脑海里的画面顺着指尖流淌到屏幕上,倘若当作文本来解读大概会有许许多多难以自洽的地方,所以全当练笔吧。不过不太应景,或者说有些讽刺的是,这些都是在上《控制论》(通识核心)的时候写的,大概在现在的日子里,我也只舍得在这些可能会点名但又不想听的课上,腾出时间来做这些“不务正业”的事情。
写到这里,突然急急忙忙的去翻第一次收到《昨日之海》的回信,找到 47 姐姐写给我的这句「相反,我觉得你一定对文学,对一些无法被量化、看不到直接结果的事情,还有对看似“散漫”“不务正业”的事情是有执着与追求的」,突然又觉得羞愧。
一个插曲,在去找邮箱的时候发现自己通过了 JetBrain 的学生认证!
某天突然想起自己高中写的某篇参赛文章,里面用到了“鸽子屋”和“老鼠屋”的意向。说实话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那是什么,那是一个巴掌大的、石板做的屋子,总是摆在一些角落。模模糊糊的,我总觉得自己很小的时候认为这些屋子都是建给鸟儿的,后来不知道听了谁给我解释,说那是用来放老鼠药的。当时总觉得有一种幻想破灭的感觉,却意外的觉得很适合做一种意象。
说起来,我总是觉得童年搬家前的记忆里,有很多难以割舍的东西。我总觉得自己记性差,背诵类的任务从来都给我带来不小的负担,但是有很多很细节的,甚至不起眼的东西会持久地烙在脑海里。而我前面提到的这种“难以割舍”,在我开始提笔记录思绪之前,就是那样一种被动的存在。
我使用“童年”,并非是在指代童年这个意象,而是指我记忆里的那段日子。而之所以总是忘不掉,大抵是觉得当下的这个时代让人解离、让人浮游,而在我记忆里的那段日子,有一种独特的胶黄质感,还有一种午后的窒息感,然而正是在这种窒息感中,我的精神才得以凝聚。
在我的印象里,我的记忆的开端,像是灵魂附身(然而在我小学的时候就怀疑是否是将某一场梦错记成记忆的开端了,而记住了记忆的开端这件事本身也散发着一种矛盾的味道),我从马路的正中央忽地飞进了,在我小学门口的铁栅栏边,送我去学校的外婆身边,一个矮小的身体里,这便是“我”这个故事的开端。
我不清楚是受到这种对过去的留恋影响,还是这种留恋是一种结果,我总是在抗拒着一些最新的事物。我将这种抗拒定义为对时代浪潮的抵抗,定义为不希望自我在变迁的方向中被同化。具体来说,我仍然更喜欢实体卡而非电子卡,更喜欢用 HDMI 线而不是投屏软件,更喜欢用邮件而非即时通讯……事实上我真的觉得后者的那些不好用,但另外一种层面上,或许我也是在警惕自己的价值观和世界观,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新的生活方式侵蚀,逐渐忘记自己最初存在的根系。
然而这种警惕往往是后知后觉的,总是出现在事后的,有时候会突然发现,自己无意识地写了半句话后开始发呆,好像是接受了 Copilot 作为我的外置思考工具。在写最上面的《片段》的时候,无意中看到了这样一段的补全: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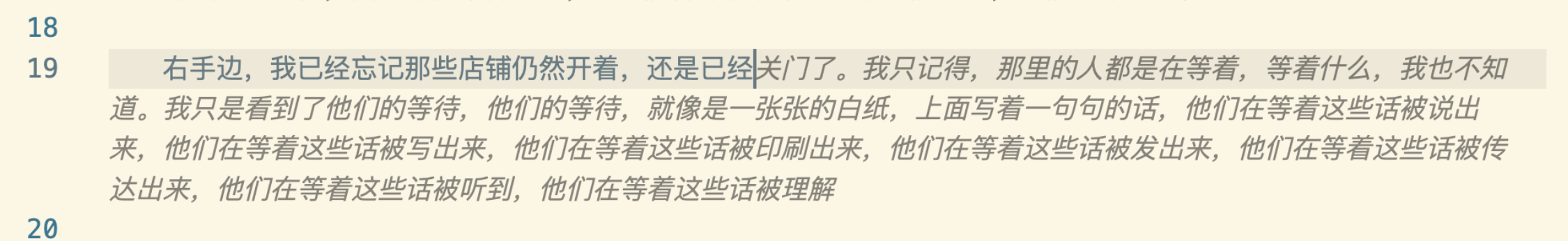
读着前面几句觉得生硬且俗套,但读到最后几句却突然觉得有几分感动。但无论如何我都不会接受这些文字成为我的内容,就好像我的肉体中镶嵌了一块宝石,也许耀眼,但绝不和谐。
阅读
最近在重读特德·姜,看到《你一生的故事》的一句话:
“有时候等待也是一件很好的事。”我会说,“有了等待,到时候会觉得更好玩。”
一方面在二刷的时候才能理解这句话背后有别的意思,另外一方面我也想到了以前在纪德的书里看到的(应该是译者序之类的东西里提到纪德说过这句话,但我并不知道实际的出处,也无法找回原文的表述,所以下面的表述只是我记忆里对这句话的复原):
完完整整地叙述我将要经历的一切。